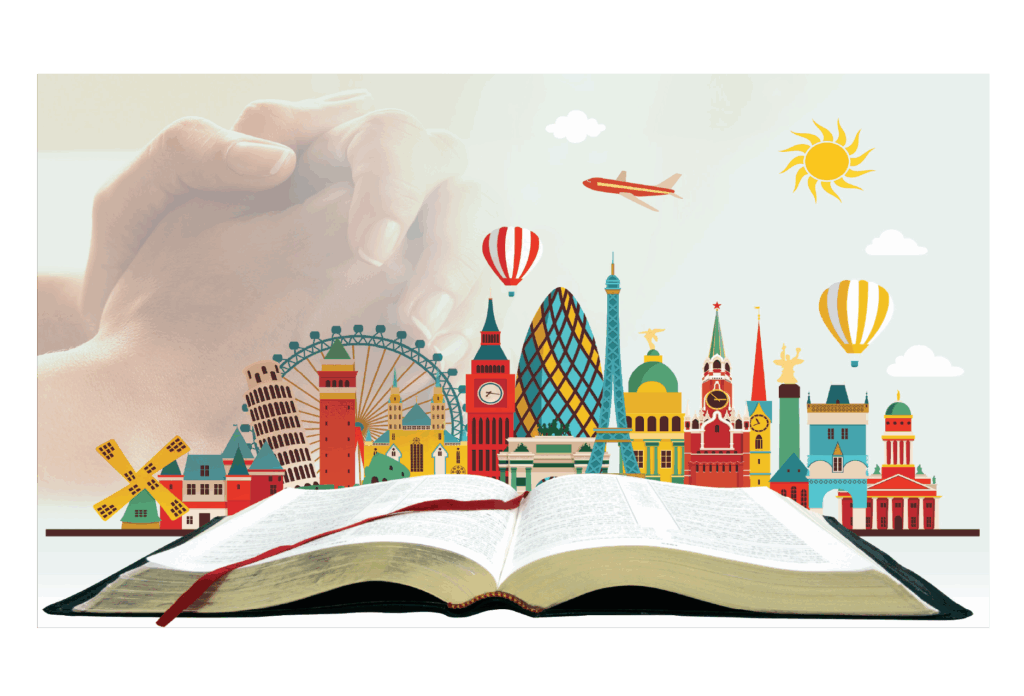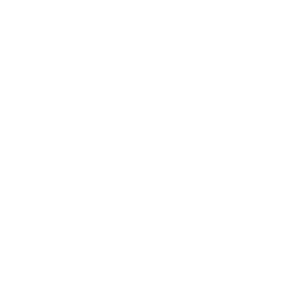走向未來─21世紀宣教前瞻
莊祖鯤牧師
在波瀾壯闊的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VM)的推動下,20世紀的普世宣教有了空前的發展。1900年全球的基督徒中歐美占83%,但是到了2010年卻降到36%。相反的,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基督徒卻都有快速的增長。但是21世紀之後,普世宣教將何去何從?這是很多基督徒關切的事情。
1. 走出後現代思潮的迷霧
從20世紀中葉從西方開始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席捲了全球,成為勢不可擋的思潮。雖然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定義與來源,學者們眾說紛紜。但是基本上可以將後現代主義視為對現代主義(也就是理性主義)的逆反現象,因為理性主義所深信不疑的觀念,後現代主義的人完全不認同。他們認為科學也夾雜著科學家主觀的好惡與成見,所以是不可靠而且有偏見的;他們追求感性多過於理性;注重當下(here & now)而非永恆價值;否定任何的絕對真理,堅持絕對的相對主義。
後現代思想不但影響了整個社會,也早已經滲入了教會,只是很多基督徒還沒有警覺到而已。其實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華人教會盛行的熱情洋溢的敬拜讚美,就有後現代的DNA;風行全球的靈恩運動是在後現代思潮的沃土裡蓬勃發展起來的;追求財富與健康的成功神學之基調,也是來自後現代思想。所以,後現代思潮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今天的教會了!
但是後現代思想一方面否定一切,卻未曾提出建設性的方案。所以當這個思想風起雲湧超過半個世紀以後,就有人在期待下一波「後-後現代思潮」的出現。但是這會是甚麼呢?這是又一個莫衷一是的問題了。然而唐朝禪宗大師青原行思所提到人生觀的三個境界,很洽當地表達了這種轉折。他說:「先是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然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後又是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在現代主義盛行的時代,人們對於真理有明確的看法,因此很篤定地「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但是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時期,真理相對化了,多數人採取否定的表達方式,所以「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了;但是當後現代思潮的盲點逐漸凸顯時,人們正在走出後現代思想的陰霾,又再度能夠「看山仍舊是山,看水仍舊是水。」
宣教學者希伯(Paul Hiebert)認為,後-後現代思想的知識論,應該是批判性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這與福音派基督徒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一方面如同實存論者承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又同時批判性地承認理性的侷限性。我們承認雖然不能看見真理的詳細全貌,卻能得到真理的「地圖」,這份地圖不是包羅萬象、鉅細靡遺的,卻能指引我們方向去找到真理。持守這種的世界觀,就能夠帶領我們走出迷霧。
2. 重拾散聚宣教的策略
現在的宣教學者認為,福音要傳遍世界可能不是藉著傳統的途徑─就是將宣教士差派到遠處的福音未達之地,去向福音未達之民傳福音。而是藉著向散居各地的各族裔民眾傳福音,然後讓他們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這就是「散聚宣教」(Diaspora Mission)。
散聚宣教是21世紀才出現的新名詞,卻是行之已久而且有效的策略。使徒行傳中各地的教會,幾乎都是從猶太人的散居地區開始的;中古世紀以修道院為中心向歐洲蠻族宣教就是一種散聚宣教的方式;十六世紀開始的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大移民,也是一種散聚宣教途徑。但是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有宣教學者研究散聚宣教的策略與應用,而溫以諾博士是其中一位先行者。
散聚宣教依據地理上的近處與遠方,與文化上的同文化與異文化可以分為四種型態:
- 本地同文化─這就是各族裔的僑居地教會;
- 本地異文化─即在僑居地向別的族裔居民宣教;
- 遠地同文化─如海歸或向別的僑居地同胞宣教;
- 遠地異文化─如華人宣教士到英國倫敦的猶太社區宣教。
在這四種散聚宣教中,第一種型態是我們最熟悉的。例如韓國在美國的基督徒約為韓僑的70%,遠高於在南韓國內的20%,因為韓國教會在接待新移民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這一點值得華人教會借鏡。第三種型態也是華人教會比較常做的,例如派短宣隊去外地向華人社區傳福音或帶領福音營。第四種型態的宣教則多數依賴專業的宣教士,他們需要語言、神學與宣教學方面的特殊訓練。
但是第二種型態─本地跨文化的宣教─卻是華人教會較陌生,卻是最有潛力的一種宣教。這種事工不需要龐大資金,而且可以全民參與。例如本地的難民接待或贊助本地其他少數族裔教會等。許多北美華人教會在草創時期,都曾受到美國教會從旁協助,如今是我們向神回饋的機會。
有一位召會的唐弟兄在1950年代帶領全家從台灣移民至巴西聖保羅。他們在當地建立了華人教會,但是也在附近一座大學城建立了一間以巴西學生為主的教會。幾十年後,由唐家第二代在牧養的這間巴西教會以及各地分堂總人數將近十萬人,但信徒絕大多數是講葡萄牙語巴西人。這是華人中做跨文化宣教最成功的典範。
3. 轉型為宣教使命型教會
宣教使命型教會(missional church)是21世紀才開始在歐美教會中廣泛討論的一個既新穎又陌生的觀念,迄今可能還沒有一本相關的書籍被翻譯成中文。當我們說神是Missio Dei時候,要知道拉丁文的Missio既有「宣教」的意思,也有「差遣」的意思。而英文的mission則除了宣教,也有「使命」的意思。所以我將missional翻譯成「宣教使命型」。有些華人教會很重視宣教,設有宣教部門和宣教基金,也支持宣教士,甚至差派短宣隊,卻往往張冠李戴地誤以為自己就是這種宣教使命型教會。
宣教使命型教會的觀念的源起,可以追溯至曾在印度宣教多年的英國宣教士紐必真(Lesslie Newbigin)。當他由印度返回英國時,非常震驚地看見「後基督化」的西方國家教會何等荒涼,因此他提出許多諍言與提醒。他在1952年的國際宣教士大會(IMC)提出了宣教使命教會觀(missional ecclesiology)。但是當1961年IMC與WCC合併後,這種教會觀被埋沒了四、五十年之久。1987年有一群有同樣異象的有識之士,在紐必真的感召下,組成了一個「北美福音與文化網絡」(GOCN),經過三年多次的研討,最終他們在1998年─也就是紐必真過世的那一年─出版了一本劃時代的書:《宣教使命型教會》(Missional Church)。從此Missional Church一詞成了許多書籍和文章的熱門標題。
基本上,宣教使命型的教會與有宣教事工的教會之最大差別,乃是宣教使命型教會是「全民皆兵」,而非只差派精兵(宣教士)上陣;而且宣教工場不僅是遠方的福音未達之地,也包括本地,要向那些「遠離教會」(un-church)之人傳福音。
傳統教會要轉型為宣教使命型教會,首先要將轉變教會的事奉理念,重點不只是將人帶到教會內,也要將教會帶入社群之中;教會不是要提供全套服務以吸引人來教會,而是主動地進入有需要的社群之中;從僅僅宣講福音,到彰顯神國度的生命。
其次,教會的核心活動要從推動事工,轉為發展同工。因此,牧者的角色也從事工的管理者轉為人才培育師,對信徒作客制化(customize)的門徒訓練。牧者從超級球星轉為教練,懂得激發人事奉的心志與恩賜,又知道如何調兵遣將,發揮團隊事奉的力量。

本文取自於北美華神季刊 148期